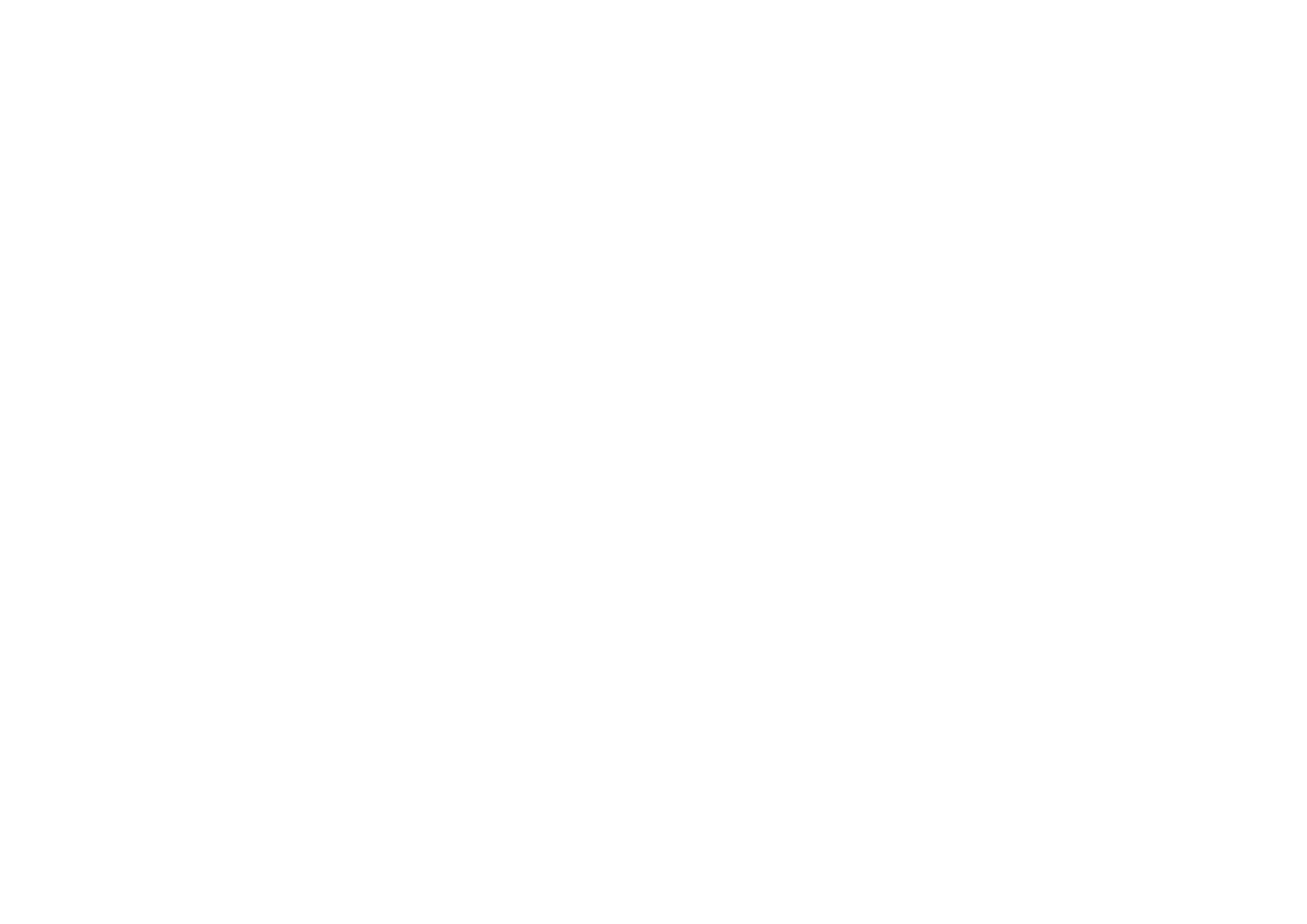「評深而論」藝評交流計劃

陳鈞潤於上世紀80年代改編莎士比亞名著《第十二夜》,廣東話對白台詞別樹一格,令人留下深刻印象,跨越40年,《元宵》仍然是很多劇迷心中的中英劇團經典。《元宵》於2024年4月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順利公演,資深戲劇研究者與藝評人張秉權曾看過1986年首演及2000年的重演,而新晉評論人邵善怡則是首次觀賞,兩人從不同角度談談這個經典復刻,從導演手法、新世代中英演員、舞台及服裝等,比較三代《元宵》。
1986年《元宵》首演教人驚豔
《元宵》大致搬用《第十二夜》的結構,兄妹遇上船難,妹妹到廣州投靠節道使賀省廬,種種愛情關係之下產生不少錯摸,引人入勝之餘亦帶出很多趣味,同時亦反映了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處境。張秉權把1986年的首演形容為「驚豔」的經驗,那次的觀賞是香港藝術節的一個劇目,當時香港話劇團成立未夠10年,而中英劇團1979年成立初期,《元宵》是中英早期改編外國戲劇成為廣東話的演出之一,當年在藝術中心小劇場以比較簡約的方式演出,以古舊風格,文字由右至左,如巡迴劇團在街頭搭戲棚,觀眾近距離觀看的除了空間,更是陳鈞潤那種靈動、流動、活潑的語言策略,把莎士比亞喜劇變成廣東話對白,又有些比較文雅的詩詞,文白夾雜。
導演Bernard Goss在香港花了很多時間與演員建立團隊精神,自成一套合作風格,演員不用很多,一個人可以演幾個角色,但演員的ensemble、整個團隊的活力是很震撼觀眾。所以在80年代觀眾的滿足感很大,既滿足於演員的表演及整體的感染力,簡約不靠佈景,而靠演員本身的活力和合作精神。陳鈞潤把背景由英國變成唐朝的廣州,有很多外商外國人居住,例如西域、阿拉伯人,唐朝是比較開放的年代,女扮男裝,或者是愛情令人盲目,彼此追求,時空選取是很合適,張秉權看首演的時候很驚豔,2000年又有看,所以三個版本,一起在腦裡出現的時候,藝術上的滿足感是大的。
感受節奏更重要於理解文字
是次演繹很忠於陳鈞潤當時翻譯的語言策略,所以裡面很多對白,尤其是階級比較高的角色,會用一些比較文雅的說話方式,也會呼應原劇本的一些詩意處理,那種語言的魅力對觀眾來說,真的難以細味,陳國慧嘗試不看字幕,但有時候因為聽不清楚,周旋於字幕與觀演感受之間,忙得有點無所適從,尤其是這次的台比較闊,看的時候就造成困難。邵善怡坐在第二排中間,看字幕就好像在看旁人,所以就很克制,瞄了幾眼然後就沒有再看,聽到大概六七成,理解意思上沒問題。如果很精細,某些字眼可能會錯過。
張秉權指出即使在英國演出莎士比亞作品,觀眾可能亦只能接收六成,台詞其實並不要緊,86年的版本是沒有字幕,而Bernard Goss和Ceri Sherlock兩位導演處理不同:86年節奏快很多,演區較小;重演版因為演區寬闊增加了走動的時間,使演出節奏變慢了。2024年演出其舞台設計可取之處是有畫卷之感,在觀眾席等開場時,看到佈景畫了高低的山勢,開演的時候就有些樂聲在外面傳過來,感覺是漂亮的,有清明上河圖的感覺,唐朝的廣州在中國南方是一個國際大都會,住了六位數字的西域人與阿拉伯人,很多人在這裡通商做生意,所以這地方某程度上跟86年的藝術中心小劇場,雖然大小相差不知道多少倍,但是也有街頭演戲之感。在英國莎士比亞時代演出時,是沒有燈光變化的,環球劇場雖不是街頭,但上面露天,也有粗樸的感覺。今次節奏較80年代演出慢,無形中提升觀眾對文字理解的要求,令他們想明白所有台詞;但是86年看的時候,就不用明白台詞,不明白亦不會錯過,不會不明白戲劇講什麼,所以節奏快的時候,你就會忘記思考、放下理性。
陳國慧覺得節奏的掌握,很影響究竟觀眾是否去看字幕,因為如果節奏快一點,或者用別的語言,包括身體、表情或者演員與演員之間能量的交換,即使我不能完整地聽到所有對白,我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氣氛。但是,某些台詞的挑戰很大,譬如他在哪些節奏、位置去停頓,又或在哪時要有一些助語詞。除了日常與巿井的部份,有一些詩詞對白,如果加太多助語詞,又好像削弱詩意,演員其實非常厲害,但演員的演繹聽起來有點辛苦。邵善怡覺得文言部分,一般都是比較生硬,可能是文言放在日常對白中就有點奇怪,但是讀到詩的時候,詩本身是有它的詩意和韻味,當感受到韻味時,是沒問題的。張秉權指出《元宵》並非每一首都是那麼高雅的詩,有一些是半鹹半淡的所謂打油詩,所以聽不明白是完全不要緊的,它不是文學水平很高,要你慢慢去細味的詩,而是有一些口語加上打油詩之間,那個感覺遠遠重要於理解裡面的內容,所以觀眾對文字不理解是真的不要緊。
《元宵》融會中西,文字靈動,陳鈞潤才氣橫溢
張秉權在看初演的時候,覺得陳鈞潤很才氣橫溢,香港劇界能夠像陳鈞潤那樣有才氣、聰明、幽默,這麼厲害的人真的不是很多,他在縱橫於中西文化、文學之間而創作。我們不妨比較三個版本的場刊,人物演員表有無英文呢?,因為導演Bernard Goss是外國人,首演場刊因此印上原來莎士比亞的英文,Orsino譯成賀省廬、Sebastian譯成石芭亭、Antonio譯成況東洋、Viola譯成石蕙蘭,中英文的發音都接近。Olivia譯成萼綠華,其實這是道教裡面仙女的名字,而非隨便譯出來,賀省廬是喜歡一個仙女,天仙下凡般漂亮,初演是鄭寶芝飾演,2000年由羅靜雯演,這次由白清瑩演,三位在賀省廬眼中都是仙女。如果我們明白萼綠華的出處時候,自然明白原來賀省廬喜歡她,是戀上一個從天上下凡來的仙女,可惜最後都抓不到;原來視對方為仙女,愛情都會落空,因為對方不喜歡你,而是喜歡自己眼中一個不是「她」的人。石蕙蘭有句台詞大意是說:「我不是你見到的我,你見到的我不是真的我,你見到的我是賀省廬的僕人,其實我不是他的僕人,我是喜歡我的主人,我是被迫來到,因為喜歡我要做好我的工作,幫主人送情信向你求愛,其實你喜歡我是你看錯了我。」愛情的真真假假是很美好的。
另一些角色譯音不那麼漂亮,Maria譯成晚霞、Toby譯成鮑莬鼙,都照顧到音和意思的關係,很古雅很漂亮,鮑莬鼙首演由平西(劉安東)演出,與孫惠芳演的晚霞是絕配,2000版由群仔(林澤群)演出,今次由朱勇做鮑莬鼙,聽起來以為是爆肚皮,其實因為陳鈞潤玩文字遊戲,很靈巧又活潑又幽默,玩中文玩英文玩到那麼絕,在80年代看這個戲時,令人驚豔,成為經典。一說到《元宵》就不會不聯想到中英,另一個團可以做《第十二夜》,但一定不夠膽做《元宵》。例如另一個有名版本是沙田話劇團在沙田戲劇節找來孟京輝製作《第十二夜》,一開場時一群演員站在台前,以急口令讀劇本裏面的台詞,對著觀眾站著講講講,大概十分鐘多一點,不斷地給觀眾講他們要講的台詞,應該是金句式重要的台詞,講完之後就跳到觀眾席向兩旁散去,然後是:「各位觀眾現在中場休息15分鐘。」當時所有觀眾都大吃一驚,還未夠15分鐘上半場就完,發生什麼事?15分鐘後回來幕升起,下面就是一個精神病院裏面的景:舞台上幾張病床。剛才站在下舞台講台詞的人進了戲內,做《第十二夜》裏面的故事,很認真地做莎士比亞的台詞,不是剛才說的急口令,但是在精神病院裏面做的,於是讓觀眾想像到:愛情令人精神失常,所以就變成認不到人,又不斷錯摸,又暗戀又想嫁主人之類,所以變成一個精神病院的故事也是合適的,這樣做了大約兩小時。
中英劇團的傳承精神
所以在香港演的《第十二夜》已經有個版本,但《元宵》只能有這個版本,這劇本太厲害了,其他劇團應該沒有意念去做,因為陳鈞潤是特別寫給中英,所以中英這次再做這部戲是好事來的。86年那個班底,當然很難再有。原來演Viola的羅靜雯在2000年的版本演出Olivia,Viola改由彭秀慧演,羅靜雯串連兩個戲。今天的藝術總監張可堅沒有參演2000年版本,但是他在86年演出賀省盧及尉遲岸汐,2024年演出月下老人,變成串聯首演和2024年重演的演員。隔了24年後再重溫Rupert的鬼斧神工,珠玉在前,是很難超越的,但張秉權坐在觀眾席看的時候,就看到劇團的傳承,滿足感就很大,再三演出可見中英劇團的傳承精神。
這次演出是比較認真的版本,無論是空間處理或服裝的演繹,造型也很非常精緻,亦有一些看來像真的打鬥場面,導演在〈導演的話〉裡有說,演員的表演策略也不是從一個玩樂的角度去處理這個作品。邵善怡認為作品在認真及玩味之間難以平衡,因為她本身也是抱著看喜劇的心態進去,但其實有很多比較文雅的對白時,對於本身接收鬧劇的感覺,其實是有點隔閡的,而比較認真的場面處理,例如打鬥格劍的場面,有真劍及真比武的場景,但其實那些動作也不是很流暢,所以認真當中有點突兀,令人有些難以進入。除了一些畫面,還有上層人物服飾上有特別精緻,例如萼綠華及晚霞的服裝是精細一點,但同一時間他們的妝容、髮型都很誇張,那種誇張和精細是有種諷刺的意味,因為剛剛說其實她應該是很漂亮的仙女角色,但是她的妝容處理令你很難有這個想法,反而她跟丑角是同一種化妝的方式,所以就會將他們的定位重疊了。可能因為唐朝的人是如此化妝的,例如敦煌壁畫或唐畫展覽都可看到那種,就產生一個距離去欣賞他們,這次變成真人,陳國慧覺得有一點看起來誇張之餘,好像跟本身難以完全配搭。
重演演出風格不一,演員各有特色
1986年在小劇場做,戲比較簡約,張秉權指出演員ensemble 是最重要的,不是說這次的演員不好,而是因為當年是Bernard Goss來到中英,第一個任務就是將全部演員訓練到他們身體語言,以至整體風格是很統一而突出。所以首演就變得很完整,這次三十多年以後,演員跟當年是截然不同的風格,那個景這麼闊,演區這麼大,服裝這麼真,比劍亦很真,語言節奏減慢,好像引導你去聽台詞是否解得通,演出就被拉散,節奏又慢,看的時候需要兼顧太多,未能集中,不知到底要看甚麼,比劍時這麼認真,但劍肯定不是刺得死人的真劍,是軟的道具,即使被刺也不會死,但又要很認真地打,亦跟戲曲不同,因為戲曲的比劍是舞蹈化,是藝術化,是美,現在好像是真,真和美是兩個不同價值,觀眾看的時候對如何拿捏會有尷尬。陳國慧認為服裝使他們走動上複雜了,要在台上更多長時間的走動,這些細節都影響表演節奏。
無論陳鈞潤的這種翻譯或者改編的方式,在現在的香港劇場來說很難再有了,但對於首次觀演的邵善怡來說,又未至於感到驚豔,甚至覺得有些地方是矛盾或不很脗合,在整個作品裡印象最深的演員,除了茅福祿就是吉慶,「吉慶」(尹溥程飾)一出來整個節奏就很輕鬆,看得很舒服,他真的帶動氣氛,與觀眾直接互動,令人很進入到作品本身。但到「茅福祿」(張焱飾)又會抽離他的輕鬆,後段令人感沉重,甚至會擔心,對於他被人戲弄是有點肉緊,但其實是不應該肉緊他,那種沉重會令人覺得不太合適。陳國慧指出這可能是導演的某種策略,未必想從一個很快樂的角度去處理,而自己對飾演茅福祿的張焱有深刻印象,事實上張焱在很多其他作品裡,都比較容易讓人有印象,除了因為身形高大之外,本身演繹喜感挺重,咬字令你覺得很有趣,一認真地說話甚至罵人,也會覺得挺有趣的,所以他演的茅福祿,令觀眾看得很歡欣,例如有很多場景,張焱都有帶動到氣氛,自己也找到與這個角色之間的獨特風格。
Malfolio譯成茅福祿,張秉權認為這譯名亦妙,音也對應廣東音,打茅波想食天鵝肉,娶個女主人,向上爬,於是就很幸福很有錢有祿,名字已經幽了角色一默,86年時是李鎮洲演的,他演法沒有這次張焱那麼認真,其實李鎮洲是極其認真,極其好的香港好演員,但他的演法能夠介乎於playful和serious之間,跳到serious那裡,然後再抽出來去playful那裡,是很快的,在一個演員身體上,我們看到兩樣東西同時出現,又playful又serious是李鎮洲演戲的特點,不會完全是那麼serious,沒有張焱那麼serious,他也是好演員,而李鎮洲因為比鄭寶芝矮一點,戀上女主人想食天鵝肉是perfect match的;而張焱較白清瑩高大,加上張焱很認真,這個對比就沒那麼完美。
莎士比亞可以喜劇之筆,寫出人心的陰暗
張秉權指出其實作品是需要有個陰暗、悲慘的角色,去襯托整個戲的喜鬧感,愛情令人盲目,這盲目清教徒也不能免,原來莎士比亞諷刺清教徒那種懶惰、懶醒、自大、好說人非,諷刺這些人,但他自己又有這樣的弱點,又被人家Maria戲弄他。所以在愛情令人盲目中,盲目到感覺活該,會看到darker side。所以莎士比亞的偉大,不在於他只寫單面簡單的好玩,而是留了一條陰暗的色塊,令到事情很立體、富色彩,但這次茅福祿好像「演多了」,他後來還要被人家鞭打,滿身傷痕,好像行刑一樣,被捆在木頭上綁住手,整件事就很重。全劇完後,張焱轉出來一起團隊合唱,已經下了妝,離開茅福祿的角色,但因為他之前太重,感覺就好像「剛才你很慘,為何可以這麼快就不慘」,慘的程度好像多了。
首演時美學上採取比較簡樸或者普通一點的策略,透過演員的ensemble一起找到能量,似乎用另一個方法,令到作品給觀眾有比較鮮活,完整的感受。這次相對來說,資源比較豐富,這次服裝上各樣都非常精細,中英用另一個策略去處理這部戲寶,從藝術上來說有其選擇的理由。張秉權作為比較幸福的觀眾,看了三個版本可作比較,相對來說視野有所不同。今年是中英劇團45週年,作為一個在香港這麼重要的劇團,搬演一個這麼重要的作品,陳國慧覺得有培養觀眾的意義;對於劇團的品牌建立,也有很正面的作用。劇團借這個作品善用自己文獻庫材料,跟一班新的演員,透過這些紀錄和文獻,把經典作品用另一個角度去演繹,對中英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好的方向。希望未來中英能有類似的嘗試,繼續重溫中英以往的戲寶,令新一代觀眾體會到:一個具有歷史的劇團,如何在從過往經驗演化至今天。